洛威尔从不掩饰自己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他被广泛认为是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主义主流诗人的主要继承人。1965年,当一位评论家把一篇文章取名为《洛威尔的时代》时,这还成不了一件特别有争议的事。但是,一个新时代正在形成。在不断升级的战争、妇女解放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的三重压力下,民主党的分裂──这个动荡的社会世界被快照式的十四行诗捕捉记录在《笔记本》(1967—1968)中──宣告了战后自由派共识文化的崩溃,而洛威尔似乎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言人。
“失去的艺术”——评《海豚信》和《海豚》[美] 兰登???·???汉默程佳 译
作家的书信价值几何?这个用钱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在《海豚信》里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次要情节中展现了出来。
1970年,罗伯特??·????洛威尔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做访问研究员,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则和他们13岁的女儿哈丽特待在纽约的家中。家务事让哈德威克感到难以独自应对,她在给洛威尔的信中写道:“卡尔,我应付不了了。我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每天的邮件越来越多,消耗的精力也越来越多。”看到“那么多琐碎、沉重而令人疲累的事情”有机会简化掉时,哈德威克便着手促成洛威尔书信文稿的出售。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对这些书信文稿“极为感兴趣”,但她更中意哈佛大学,因为洛威尔与哈佛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石溪分校也不是洛威尔的第一选择,但他们开出的价格更高,而他需要钱。哈德威克于是把石溪分校的报价透露给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遂提高了价码。一番周折过后,哈佛大学于1973年买下了洛威尔从童年时期一直到1970年的书信文稿。
但在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太多,哈德威克无心庆祝。第一次查看洛威尔那堆得满满当当的文件柜时,她是盼着他快点回家的。但他没有。他爱上了英裔爱尔兰作家卡洛琳·布莱克伍德,留在英国和她在一起了,即使1970年7月他因躁狂症发作住院之后,也不愿回头。布莱克伍德避走爱尔兰时,哈德威克去找过他。1971年,布莱克伍德和洛威尔的儿子谢里丹出生。一年之后,洛威尔与哈德威克离婚,与布莱克伍德再婚。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写自己在布莱克伍德和哈德威克之间挣扎的诗,这些诗将在1973年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出版,取名为《海豚》。其中一些诗引用了,或者说似乎引用了哈德威克在这一时期写给洛威尔的信件──那些表达了她的悲伤和委屈的原始信件。
到1972年7月,随着向哈佛大学出售书信文稿的事宜向前推进,哈德威克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她这是替一个要与自己离婚的男人做事,而且这个男人还在写一本书,讲述他决心离婚的故事。此外,她告诉洛威尔,书信文稿里包含了“所有我写的信,除了你写给我的那些之外”。其中包括哈德威克写的80封信,168封洛威尔单独写给她的信,还有许多与她有关的信件。“我本来是应该自己出面去和哈佛谈这件事的,”她明白过来了,但“我竟然没能够为自己争取一下权利,而且恐怕当时还有些过于感伤……”
书信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如同礼物。它究竟应该属于谁,属于写信人还是收信人?谁来决定可以用它做什么? [1] 当洛威尔的朋友们传阅《海豚》手稿时,这些问题又冒了出来。斯坦利·库尼茨告诉洛威尔说,他觉得有些段落“太丑陋了”,读起来“太残忍了,亲密得太残忍了”。伊丽莎白·毕肖普用大写字体和斜体字斥责洛威尔:“人自然可以把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不管怎样,总会有人这样做──但是利用这些信,你不觉得是在毁掉某种信任吗?假如你事先得到了允许──假如你并不曾改动它们……如此等等。但艺术根本不值那么多。”
[1] 在一个著名的法律案件中,J·D·塞林格试图阻止伊恩·汉密尔顿(洛威尔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出版塞林格的传记,声称汉密尔顿的书稿引用并转述了他未发表的信件,侵犯了他的版权。这个案件先是汉密尔顿胜诉,塞林格不服上诉后获胜诉。──原注
这本书于1973年公开出版后,哈德威克身心受到重创。她给洛威尔的出版商罗伯特·吉鲁克斯写了一封极为愤怒但言辞模糊的恐吓信。她还告诉毕肖普,《海豚》和那些评论“伤我至深”。“我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她在给洛威尔的信中写道,“成天疑神疑鬼、担惊受怕,不知道你又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比如说把这封信也用到你疯狂的诗作中。”
展开全文
洛威尔在诗集《海豚》中引用的哈德威克信件并不在哈佛大学拍得的书信文稿中。哈德威克告诉洛威尔,她至少想“看一看那些[你说是我写的]信。你把我的声音放了进去。可是我记不得了,我只想看一看你是怎么利用它们的”。但洛威尔从未归还这些信,连复印件都没寄给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信似乎遗失不见了。哈德威克于2007年去世,她在世时一直认为是布莱克伍德在洛威尔 1977年去世后将这些信件销毁了。
事实上,布莱克伍德挽救了它们。1978年,她将所收集的102封哈德威克写给洛威尔的信件寄给洛威尔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弗兰克·比达特。比达特按照他自认为是洛威尔的意愿行事,将这些信件保存了10年之久,然后又将它们存放在哈佛大学,并要求“由霍顿图书馆代为保管,直到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离世”。哈德威克的信件先是在《海豚》一书中在未经她允许就被公开示人,后又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保存在了哈佛大学。
*
1977年,洛威尔在生命最后6个月里的健康状况很差,他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躁郁症,自1949年以来,他因这两种疾病住院不下20次。他和布莱克伍德的婚姻破裂了,他不知不觉又和哈德威克生活在一起了。“这事说来也挺奇怪的,”哈德威克认为,“我们只是在一起过日子,过得还很舒心惬意。”那年夏末,洛威尔去了爱尔兰看布莱克伍德,然后飞回纽约。他是打出租车去哈德威克的公寓的。当司机把哈德威克叫到车旁时,她发现自己的前夫已经死于心脏病发作。当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幅卢西安·弗洛伊德为布莱克伍德画的画像。即使洛威尔是出了名的自我戏剧化,也总是给亲近的人带来痛苦,他也不可能编造出这样的结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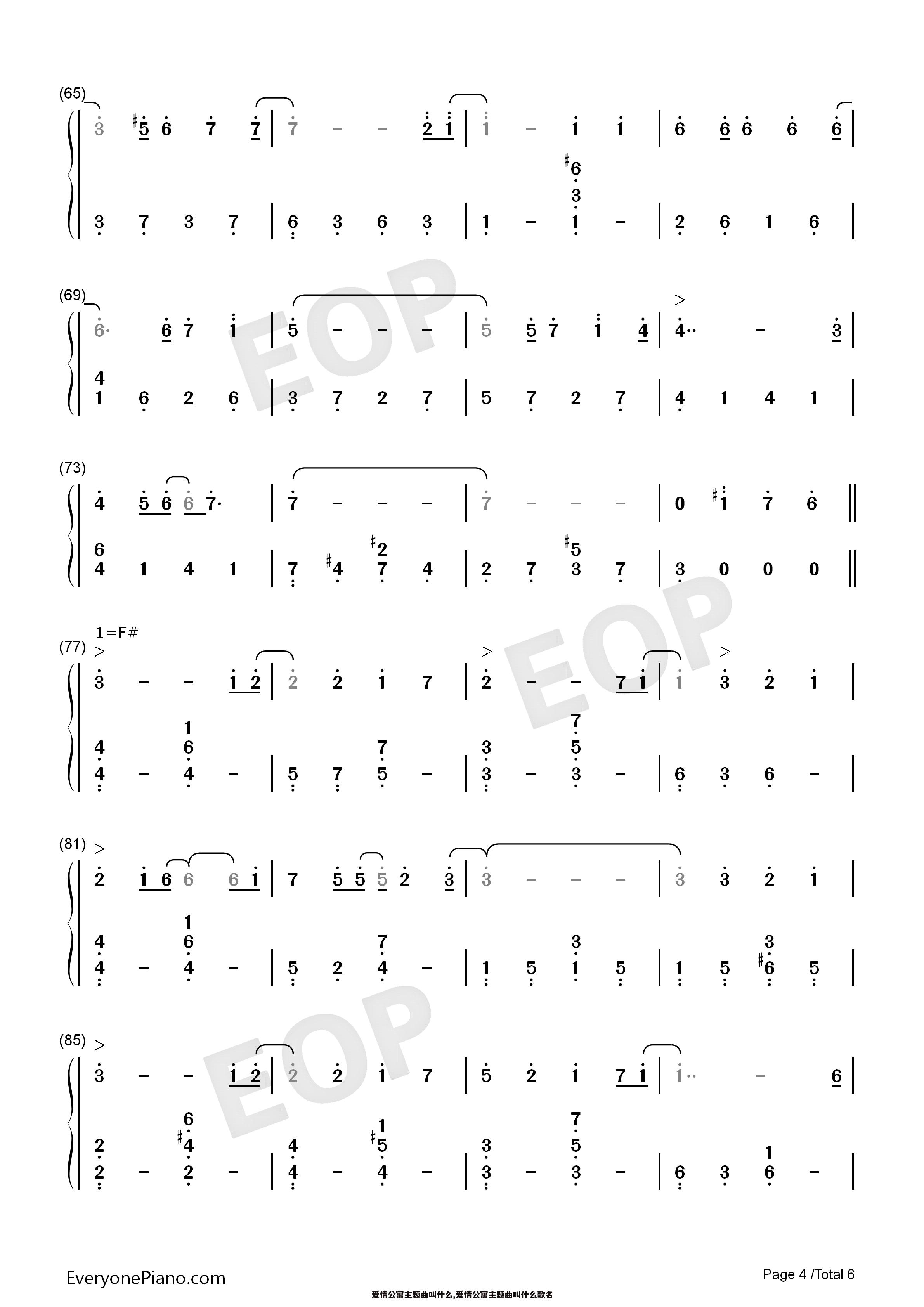
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给哈德威克的信,都收集在《罗伯特·洛威尔的书信集》中出版了,该书由萨斯基娅·汉密尔顿于2005年编辑而成。现在,在这本《海豚信》中,汉密尔顿又编辑了哈德威克的书信,将其与洛威尔写给她的信逐一匹配,两个从未完全分开也从未完全重聚的人,便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再次联系在一起。这样做正合适,因为他们之间的沟通不太稳定,也不同步。信件交叉、问而未答。但相比他们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之间持续的通信需求。“是啊,写信是件很奇怪的事,”哈德威克在写给洛威尔的一封信的开头这样说道,“其实我们之间不存在给对方回信的概念……就只是写一种叫做信的文章而已。”
这张全家福摄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威尔去世时携带的公文包中放着这张照片。
哈德威克和洛威尔之间的通信本身足以构成一本厚厚的书,若《海豚信》没有收录“他们那个圈子”的作家之间的往来信件,它或许并不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么引人入胜、意义重大。哈德威克和洛威尔时常情不自禁写下一些尖锐而又动人的信件。但不总是如此。在他们走向离婚这场常见的灾祸时,每一步都有注解,这种感觉就像是在观看火车失事时的一个慢动作镜头。他们专注于自己,顾着彼此,顾着女儿,担心各种税务,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因此陷入了与家庭角色(被抛弃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出轨丈夫)相配的陈词滥调中。汉密尔顿及时引入其他声音抵消掉这种效果,将画面放大了。
有些声音是我们所熟悉的。毕肖普那封信中说的“艺术根本不值那么多”,是毕肖普批评中为人熟知的论调,因为它明确了她和洛威尔在伦理上美学上的差异。对毕肖普来说,关键并不在洛威尔写哈德威克,甚至引用她的信件也没什么错;问题在于,他改动了她的信件,“不交代清楚何为事实何为虚构就去讲故事”。洛威尔在给比达特的信中称毕肖普的信是“一篇批评杰作,虽然她对这种披露表现得极度神经质(上帝呀我错了,只说这一次)”。这句评论说明了毕肖普的言辞极其激烈,还破天荒把那个经常撒野的躁郁症患者洛威尔放到了能够吸纳别人强烈情绪的位置上。
这些信件如今可以和毕肖普就《海豚》与哈德威克的往来书信一起阅读了。毕肖普直到该书出版后才联系哈德威克。她轻轻敲了敲哈德威克那间充满屈辱和愤怒的小房间的门(“希望这封信不会让你觉得唐突或者冒犯”),为自己没有阻止洛威尔的所作所为而道歉。所以三个月后,当毕肖普反过来指责哈德威克时,还真是有些令人惊讶。她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纸的信,详细描述了哈德威克如何在一篇文章 [2] 中歪曲了自己的情人洛塔·马克多·苏亚雷斯,含蓄地指责哈德威克对洛塔做了洛威尔对哈德威克所做之事(尽管哈德威克只是顺带一提,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提)。
[2] 即《在缅因州》,1971年10月7日刊于《纽约书评》。──原注
哈德威克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同情地说:
但凡是我们自己或是一个挚爱的老友,突然被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曝光在众人面前,换谁都难免觉得特别不舒服,甚至是惊恐,因为知道事实绝非如此。……你是不知道,我其实非常害怕将来,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记,还有《丽兹传》,都不知道自己会被说成什么样子。“卡尔”就更不用说了,他真正的存在和本性永远都不会有人触及到。
但凡是我们自己或是一个挚爱的老友,突然被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曝光在众人面前,换谁都难免觉得特别不舒服,甚至是惊恐,因为知道事实绝非如此。……你是不知道,我其实非常害怕将来,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记,还有《丽兹传》,都不知道自己会被说成什么样子。“卡尔”就更不用说了,他真正的存在和本性永远都不会有人触及到。
尽管她强烈谴责他对待她的方式,但她对卡尔仍抱有同情──他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纠结。
在这封信的这个点上,哈德威克变成了文化批评家,超越了个人的恩恩怨怨,“这些[对一个人的]挪用”表明“与一种日益增长的宣传需求有关,并相信宣传就是一种价值;也与注意力这个概念有关。如果你只想要它为你所用,那么就不要希冀其他人也会和你想的一样。你一直在说,”──她脑子里的声音一定是洛威尔的──“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又不是针对你的!似乎对此有且只有一个评判标准……到最后这就意味着,你认为任何人都是不真实的。”
哈德威克提到“宣传就是一种价值”以及“注意力这个概念”,将关于《海豚》的争议置于一个奇观社会中,在这个奇观社会,个人身份有一定的公开表演性质,因此是失重的、可塑的,是一种现实效果。洛威尔想从她的信中得到的,毕竟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感受。正如他在毕肖普面前为自己辩护时所解释的那样,“我认为正是这些书信诗成就了这本书,至少通过这些书信诗的衬托,丽兹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并非我凭空臆造”。
阿德里安娜·里奇认为洛威尔在《海豚》中对哈德威克的处理表现出一种“夸张而又无情的男子气概”。在为《美国诗歌评论》撰写的书评中,里奇引用了这部诗集中最后一首十四行诗《海豚》,洛威尔在这首诗中承认,“与自己谋划人生时太过随意,/不免伤及他人,/不免伤及自己──”,然后就评论道:
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纯粹就是扯淡的雄辩,是一本残忍而浅薄的书的拙劣借口,在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之间取得平衡,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做法──但问题仍然是──居心何在?
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纯粹就是扯淡的雄辩,是一本残忍而浅薄的书的拙劣借口,在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之间取得平衡,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做法──但问题仍然是──居心何在?
《海豚信》填补了这一措辞激烈的公开指责背后的个人历史。里奇和洛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是好朋友,当时她“穿着丽兹穿过的孕妇装,不辞辛劳地奶孩子,不堪其苦”,是洛威尔夫妇成了“我与诗歌、与自己的世界最紧密的联系……在坎布里奇我才不至于被繁重的家务和那套教授做派压得喘不过气来”。里奇和丈夫阿尔弗雷德·康拉德当时住在坎布里奇,后者是一名经济学教授。洛威尔离开哈德威克后不久,康拉德自杀了。哈德威克和里奇都经历了丧亲之痛,并在新的独立中建立起联系,年轻、政治上激进的里奇为哈德威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海豚》出版之前,在里奇和洛威尔的通信中,我们看到两个人──我们也看到文化本身──正在迅速转变。康拉德离世之后,洛威尔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他从里奇的困境尴尬地转向自己的困境,提到自己“有了新女友”,“我想离婚大概是在所难免的,虽然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有些东西却永远无法挽回了”。里奇表示后悔没有与他们经常保持联系,但她随后就在信中对他的言论提出了质疑,坚决谴责他又有孩子的行为(“现如今在历史上,生孩子虽然是平常事,但做起来却是不寻常的”),并在信末郑重宣告:“我对于描写未来的诗歌比较感兴趣。”
洛威尔回敬道:“未来的诗歌?我不确定自己读过这类的诗。不过我认为自己读的还不少──兰波、《奥赛罗》,所有令诗歌竭尽所能的作品。”至于生孩子,“我觉得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时代不同了,今时往日不可同日而语。”洛威尔是可以支持那些声明的,但里奇的信“让我很困扰”,他对哈德威克说,并以辩解、冷嘲热讽的口吻补充道,“女性问题似乎压过了黑人问题。”这句话加深了他和里奇之间的隔阂。
*
《海豚信》副标题中的“他们那个圈子”,指的是洛威尔和哈德威克的美国圈子,而不是洛威尔和布莱克伍德的英国圈子。洛威尔爱上布莱克伍德时,她38岁,是个富有、迷人且放荡不羁的女子: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前妻兼模特,作曲家伊兹雷尔·契考维茨的妻子,吉尼斯家族的一员,女演员,有时被认为是与穆里尔·斯帕克齐名的记者兼作家,三个女儿的母亲,酒鬼。但在这本书信集中,她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只呈现在几封书信和别人对她的评价中。洛威尔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必须从他写给哈德威克的信中来推断,而且在信中他也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
尽管如此,一幅图景还是浮现出来了。1970年,牛津大学将洛威尔带回到过去。“万灵中学完全没有第二性存在,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14岁,就跟在圣马克中学度假似的。”圣马克中学是他在马萨诸塞州读高中时的寄宿学校。后来的埃塞克斯大学是学生抗议活动的中心,与“万灵学院”那些不教书的精英的世界相去甚远,即使在埃塞克斯开始教书之后,他仍觉得英格兰是一个田园式的修心静性之地,与纽约“充斥着世俗的喧嚣、重金属的气味,还有吸食冰毒的乱象”形成鲜明对比。他喜欢被人吹捧:他觉得与美国相比,他在英国的崇拜者是美国的12倍。最重要的是,恋爱满足了他对发掘诗歌“新题材”和“新起点”的需求,尽管一切可能早已完全按照剧本写定。
在创作《海豚》的时候,他同时也在对《笔记本》 (1967—1968)中的诗歌进行修订和补充。修订之后该诗集分成《历史》和《献给丽兹和哈丽特》两本书,于1973年与《海豚》同时出版。洛威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创作无韵的十四行诗,以捕捉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他对越南战争最激烈时震动美国的事件的直接反应。1970年,他出版了一个修订版,标题还是《笔记本》,但日期没了,不再突出这本书的时效性。当他同时出版这三本十四行诗集的时候,公众事件和私人内容是有进行分类的,即时性诗学被纪念性主题所取代。“这三本书称得上是我个人的代表作品,”洛威尔对毕肖普说,“是最优秀的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会被称为最优秀的作品。”这种含糊不清的限定,表明他意识到,尤其是他在给毕肖普写信时,他意识到创作一部“巨著”的野心将会受到质疑。毕肖普的那封“艺术根本不值那么多”的信就是对这封信的回复。
洛威尔从不掩饰自己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他被广泛认为是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主义主流诗人的主要继承人。1965年,当一位评论家把一篇文章取名为《洛威尔的时代》时,这还成不了一件特别有争议的事。但是,一个新时代正在形成。在不断升级的战争、妇女解放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的三重压力下,民主党的分裂──这个动荡的社会世界被快照式的十四行诗捕捉记录在《笔记本》 (1967—1968)中──宣告了战后自由派共识文化的崩溃,而洛威尔似乎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言人。洛威尔曾积极参与反战运动,热心支持尤金·麦卡锡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在前往英国时,他退出了美国的政治活动。
《海豚》的争议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它反映了当时一种文化秩序上的情感与价值观,这种秩序刚刚出现,所涉及的东西远不只是更换掌门人这么简单。毕肖普和洛威尔去世后的40年里,他们的声誉发生了逆转。在此之前,毕肖普还一直是个次要的、从属性的人物,如今,她在关注度和声望上都盖过了洛威尔,这就表明人们需要对诗歌的价值和艺术本身的价值进行基本的重新评估。这种重新评估涉及到文化的民主化和政治化,会引发对权力和特权的怀疑和批评,而那似乎是身为波士顿名门望族的洛威尔与生俱来的权利。
伊丽莎白·毕肖普(大卫·勒文 绘)
但洛威尔是个复杂的人,他作为诗人的特殊力量,正源于他对自己所代表的权力和特权的质疑。在《生活研究》 (1959)最后一首诗《臭鼬的时光》中,洛威尔以消除戒心的简单口吻写下“我的脑子不对劲了”:
有辆车内的收音机在低声哀诉:
“爱啊,漫不经心的爱……”我听见
我染病的灵体在每个血球里啜泣,
仿佛我的手扼住了它的喉咙……
我自己就是地狱;
此处无人──
有辆车内的收音机在低声哀诉:
“爱啊,漫不经心的爱……”我听见
我染病的灵体在每个血球里啜泣,
仿佛我的手扼住了它的喉咙……
我自己就是地狱;
此处无人──
崩溃带来内心的动荡起伏。通过把躁郁症作为创作题材,洛威尔书写该观点并从其切入写作的能力,表达了他对无上之“我”的不信任,对诗歌伟大概念的矛盾心理,以及他自己想要变得伟大的野心。《生活研究》认为,身份是情境性的、不确定的;该诗集直接将自我认识看作是某种与之共生但不太令人舒服的东西,需要忍受它而不是成就它。
*
就像艾略特和庞德的作品一样,洛威尔的诗也是由引语、翻译、典故和其他口头借用词组合而成的。《臭鼬的时光》就很有代表性,里面充斥着其他的文本和声音:十字架上的圣约翰、《福音书》、惠特曼的一则轶事、蓝调标准歌曲《漫不经心的爱》,还有弥尔顿的撒旦,这些都是洛威尔在评论这首诗时自己提到的。
但洛威尔对女性声音的使用是这种总体偏好的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毕肖普强烈反对他使用哈德威克的信件,不可置否地表明了她对他在诗中使用她的作品的态度。当洛威尔的诗《呐喊》出现在1964年出版的《致联邦死者》中时,他附了一条注释,承认这首诗“完全归功于伊丽莎白·毕肖普那个美丽而平静的故事《在村庄》。但“完全”一词把这事给轻描淡写了。毕肖普的一篇散文就这样被压缩成了若干诗节,将她关于母亲发疯的自传体故事/回忆录缩减为她故意不写的、情节夸张的自白诗。后来,洛威尔又把毕肖普的一封信改写为一首十四行诗发表了,把毕肖普从未用自己声音抒写过的焦虑和痛苦归于她本人。他再一次把毕肖普变成了一个更像他自己的诗人。
洛威尔以妻子为原型创作的关于女性角色的诗更是充满争议,令人不安。洛威尔这个当时就很可能患有躁狂症的人,就曾因妒火中烧攻击过他的第一任妻子琼·斯塔福德。在1951年出版的长诗《卡瓦纳家的磨坊》中,他讲述了一个名叫安妮的妻子回忆的场景,她强迫丈夫哈里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生活研究》中排在《臭鼬的时光》之前有一首诗叫做《谈及婚姻的烦恼》,是一首十四行诗,写了一个妻子对她“喝高了的丈夫”和“他单调乏味的性欲”的愤怒。诗一开始就公开描述了洛威尔和哈德威克婚姻状况,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就面临着他的疾病的压力。
在这些诗中,洛威尔通过他伤害过或考验过的女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通过她们的声音来评判自己是否具有攻击性,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攻击性,他挪用了她们的观点──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自己“无情的男子气概”的矛盾心理。他作为诗人的长处之一就是能够以不可思议的客观性观察自己。《海豚》的最后一句就是个例子:“我的双眼已目睹我的手工之作。”他的语气很难确定:自我指责、自我赞赏、实事求是,还是三者兼而有之?在《海豚》中,他似乎需要通过侵犯哈德威克的隐私才能获得这种视角和随之而来的模糊性。对洛威尔来说,艺术至少值这么多。
后来,哈德威克又继续给洛威尔写信。1976年他出版了《诗选集》,其中也选入了《海豚》中的书信诗,此时她的愤怒已经减弱为强烈反对:“当然,真正让我介怀的是那些仿佛出自我口的话。”她一直认为那些书信诗写得很差劲。作为书评人,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知毕肖普:“我就不明白了,他足足花了三年工夫,结果还是留着一堆愚蠢之词、轻率之语,那些糟糕的诗句还在那里,没有删除。他这是为了我们大家去伤我的心呀。”哈德威克这样评价有些苛刻,但说得不无道理。洛威尔写诗喜欢追求令人惊叹的意象和适于引用的警句,这两个特点《海豚》兼而有之。但哈德威克的书信却不一样。它们是散文式的,很生动,能自圆其说。只摘取其中的片段,把几页长篇大论或悲叹变成一首十四行诗,就会失去声音的独特品质,留下诸如“你丢下两栋房子,两千册书”或“爱,被他的谜之初心彻底击败”之类的句子,所营造出的戏剧姿态也就悬空无着落了。
《海豚》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发生婚变的普通故事,也许更适合作为艾丽丝·默多克 [3] 开的玩笑,不适合洛威尔用来写成庄重、近乎神话式的自传。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个桥段只是为了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借口。编辑汉密尔顿通过这部诗集的新版本把整个故事讲述了出来,新版本包括1973年出版的《海豚》,以及1972年在毕肖普和其他朋友间传阅的以复印或抄写形式呈现的初稿。洛威尔改变了故事中事件的顺序。但他对局部的修改更值得深思。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他的重新思考和所做的调整,他深陷于词语选择的困境之中。汉密尔顿称赞他的诗歌“仅用一种姿态便巧妙地捕捉到情感和经验的复合和结合”。洛威尔的诗歌很好地做到了这点,这是评价《海豚》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尽管写作这本书感觉有些刻意,是故作高潮,渴望其成为一部巨作。该书1974年荣获普利策奖,当时的评委是安东尼·赫克特、洛威尔的朋友威廉·阿尔弗雷德以及格温多林·布鲁克斯,前者承认自己心情复杂,后者则明确表示反对。
[3] 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英国20世纪著名的小说家,被誉为“全英国最聪明的女人”。──译注
洛威尔接下来的一本书《日复一日》也是他最后的绝唱,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少有人对它进行讨论。也许由《海豚》引发的持续争议和洛威尔的突然死亡将其光芒给掩盖了。又或者,《日复一日》是关于未来的诗歌,我们现在才有机会去欣赏它。凯蒂·彼得森在《洛威尔诗歌新选》(2017)的序言中给出类似的推荐语。彼得森写道:“这位洛威尔很清楚,持久性有别于激将法。”“作为一个抒写人的日子 (the human day)的伟大诗人,他懂得易逝性,因此也懂得每一个崭新时刻的惊奇”。《日子》开头一节这样写道:
好神奇
这日子依然在此
犹如闪电现于一片旷野,
坚实的大地,并短暂
泅泳于变化之中,
鲜活恰如人初生时
好似藏红花开遍大地。
好神奇
这日子依然在此
犹如闪电现于一片旷野,
坚实的大地,并短暂
泅泳于变化之中,
鲜活恰如人初生时
好似藏红花开遍大地。
《日复一日》延续了《海豚》的生活叙事,但情节松散,没有刻意控制情节。在该诗集的跋诗《结语》中,洛威尔哀叹:“有时候,我所写的一切/因了我这老套的艺术眼光/像是一张快照,/俗艳、迅速、花哨、被归了类。”但他通过提问自己,提问那个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为何不说出发生的一切?”,为自己的自传性写作做了辩护。
我们是可怜的过客,
被其警告要给予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形象
他的活着的名字。
我们是可怜的过客,
被其警告要给予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形象
他的活着的名字。
洛威尔没有在诗中指明,但引用了这个问句──“为何不说出发生的一切?”──哈德威克在他写《生活研究》遇到瓶颈时,曾给了他这个建议,他觉得很有用。在《结语》这首诗中,哈德威克几乎说了最后一句话。
*
听说洛威尔爱上了布莱克伍德,不回家了,哈德威克气得一顿大骂,指责他在英国生活得“就像寄生虫一般”,放弃了自己作为哈丽特父亲和“一位优秀的美国作家”的责任。但她知道,责任的召唤对任性之人少有作用。所以在这封信的最后,她已准备为未来做些打算,宣布说:“我想要靠写作挣钱,当个女作家。”
这一实际目标激励着她向前迈进。成果是《诱惑与背叛:女性与文学》,这本文集,至今仍让人感觉新鲜而有意义。还有一本独树一帜的《不眠之夜》,人们很容易把《不眠之夜》称为一部小杰作。但正如它拒绝宣称自己是一部小说或是一部自传一样,要把它归为“杰作”或“次要作品”划分等级也实属不易。
在写给洛威尔的一封信中,哈德威克不经意地挑战了他自白诗的前提,她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在写自传,但生活不会愿意向我们讲述\保证/哪一时期占比最重、哪个行为能反映真实的想法、它要表达什么。”她还说:“我才会觉得,你把自己的生活看作一本书真是荒唐。”《不眠之夜》就体现了这些想法。她着手写这部书,一开始就为洛威尔和他们的婚姻来了篇“相当于一个受虐狂写的颂文”,回忆洛威尔在精神崩溃后重拾写作的决心。
她对这个开头不满意。当她在信中提到自己这些疑虑时,洛威尔惊呼:“你做什么都行,只是千万不要把你的《笔记本》给烧了。我还希望能活在那里面呢。”──这部作品就是后来的《不眠之夜》──“在我变脏之后很久。”然而,她撕毁了笔记,继续写,但写的不再是洛威尔,而是她在写作过程中被观察到的自己:“六月份了。这是我方才决定要用此生去做的事。我要这么做,过这种生活,我今天正在过着的这种生活。”第一章的早期版本总结道:现在,我的小说开始了。不,现在我开始写我的小说了──但我不能决定是该称自己为我还是她。”哈德威克修改了这段文字,但叙述者对主体的模棱两可仍然是《不眠之夜》的核心。在《不眠之夜》中,事情的发生带有偶发的随机性和命运的最终性,人物出奇地平淡,仿佛唯一可能看到他们的就是外部视角。
入选“纽约书评经典”系列的《不眠之夜》
《不眠之夜》是哈德威克关于未来的诗歌。在这部“转化甚至扭曲记忆的作品”中,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线,只有起伏不定的影像、花絮和人物速写,在时光中前后游移,不可预测。叙述者包括她的阅读笔记,她对记忆和写作过程的反思:“如果一个人知道要记住什么或假装记住什么就好了。你想要从已失去的东西中得到什么,只需做个决定,它自己就会出现。你可以把它像罐头一样从架子上取下来。也许吧。”事实证明,仅仅是说出发生的一切,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这本书里有许多写给朋友的信,祝语后面的署名是“伊丽莎白”。这个策略很重要。哈德威克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给一个缺席的收信人写信;信如何让我们同时与自己又与他人交谈;在我们的通信中,自我是各种场合与诉说的混合物,因此是碎片式的,有点像拼贴画。
《不眠之夜》中最重要的收信人是“最亲爱的M”。《海豚信》表明,启发伊丽莎白给M写信的,是哈德威克给玛丽·麦卡锡写信的这个举动。麦卡锡是令哈德威克心灵感到慰籍的一位朋友,她既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位作家,这点让哈德威克很是钦佩。
如果这种钦佩还有另一面的话,那就是哈德威克跟洛威尔说的俏皮话:麦卡锡的生活“就好像是陪着总裁和董事长主持会议一般”。这样的画面与哈德威克在《不眠之夜》中描述自己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叙述者是一个“对生命服从万有引力定律、有下沉倾向持同情态度的人,像风筝一样轻柔而缓慢地下落,或者猛烈地折断、粉碎”。这本书给麦卡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她也记下了哈德威克的实验主义所暗示的对她自己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批评:“与你相比,我那本情节拖沓、半似逼真的小说更像是一台碎骨机。”最重要的是,麦卡锡对哈德威克如何处理洛威尔问题的解决办法印象深刻:“结果你直接把他避开了,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但哈德威克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她的解决办法更为激进。她把他当作一个边缘人物来写。叙述者在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时是这样说的:“我那时是‘我们’。工作了一天之久后他在开玩笑,微笑,喝着杜松子酒,滔滔不绝地谈论‘弱者的暴政’。”

读者一直期待着丈夫归来,但他只出现了几次。最完整的描写是在倒数第二章,但这一章写的不是他,而是伊丽莎白多年来一直依赖的女管家们,仿佛她们与一家之主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似的。哈德威克对这些职业女性的同情和清晰的刻画是有灼伤力的:“乔赛特的敏捷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灾难。童年时代遭受殴打。”还记得乔赛特对伊丽莎白丈夫在精神崩溃后逐渐恢复的一段描述:
先生今天早上好吗?乔赛特会说。先生吗?敢问我一定要把他掉得一塌糊涂的棕色头发染成红色吗?没几个人有这种发色的。裤子和夹克乱搭一气,脚塞进扯长的袜子里。和善地笑了笑,口中那两排短短的牙齿,像极了他母亲的短牙齿。
先生今天早上好吗?乔赛特会说。先生吗?敢问我一定要把他掉得一塌糊涂的棕色头发染成红色吗?没几个人有这种发色的。裤子和夹克乱搭一气,脚塞进扯长的袜子里。和善地笑了笑,口中那两排短短的牙齿,像极了他母亲的短牙齿。
在乔赛特的故事再次出现之前,也没有更多...于他的内容了。
哈德威克天生“对生命服从万有引力定律的倾向持同情态度”,这点同样表现在她对“掉得一塌糊涂的棕色头发”的感觉中,表现在她对自己的清洁工那极为迅速的反应的感受中。还请注意她那迅捷的文笔:犀利的精确度预示着她自己即将面对的各种严重灾祸。但哈德威克绝不是一个受害者。如果能够创作出像《不眠之夜》这样的作品,且避免成为由总裁和董事长的陪衬,那么婚姻被打破就是一份馈赠。当然,洛威尔也知道这一点,这种知识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创作了《臭鼬的时光》《日子》以及其他伟大的诗作。对,我们就这么称呼它们吧,就像哈德威克那样。
原文刊登于《纽约书评》 (2019年12月19日 )
/ 点击图片跳转购买大雅·洛威尔系列 /
|兰登·汉默(Langdon Hammer,1953—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耶鲁大学教授。他研究诗歌文化史,对诗人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主讲的耶鲁公开课《现代诗歌》在网上很受欢迎。著有《詹姆斯·梅利尔传》和《哈特·克莱恩与艾伦·泰特》。
|译者简介:程佳,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英国班戈大学R.S.托马斯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译著有“洛威尔系列”(《臭鼬的时光:罗伯特·洛威尔文集》《海豚:手稿对照本,1972—1973》《海豚信:1970—1979》等),卢契亚诺·贝里奥的《记忆未来》,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的功能》,以及诗歌《R.S.托马斯晚年诗选:1988—2000》(2014年)、《R.S.托马斯诗选:1945—1990》(2012年)、《R.S.托马斯自选诗集:1946—1968》(2004年)、《她把怜悯带回大街上:丽塔·达夫诗选》(2017年)等。
题图:Elizabeth Hardwick and Robert Lowell in Mary McCarthy’s garden, Castine, Maine, 1977. (Castine Historical Society)
策划:杜绿绿 | 排版:阿飞
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注明个人信息
“我痛恨它们,但这些该死的东西也是我的生活”
批评家应该让自己的利舌用于赞美
无人见到你幽灵般的 假想恋人